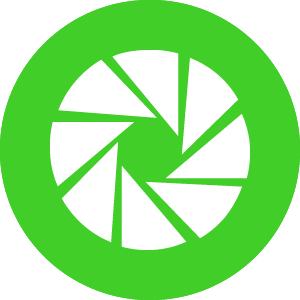71岁的沙俊起,最近的生活规律有些变化。上午,他还是坚持打网球锻炼,随后去医院打吊瓶输液——先是因为感冒,后来是治疗过敏;下午,他走进校园,带着孩子们开展足球训练——41年来,这既是工作也是爱好;晚上,这位开远市足协、永利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要么审核弟子的教案,要么誊写自己的教案,要么阅读足球书籍,要么观看足球比赛……
这个冬季,即使在炎夏暖冬著称的开远,也比往年要更冷一些。得病的另一原因显而易见,沙俊起笑着说:“人总会老的,身体也不比当年喽。”当年,如果不是爱上足球,当年,如果不是命运安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经历这样的足球人生。
天津,想当教练的少年
1950年出生的沙俊起,打记事起就喜欢足球。工厂学校、大街小巷,似乎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踢球的大人小孩。当然,天津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是民园体育场,一有全国甲级联赛这类比赛,那里总是挤得人山人海。“票价是几分还是一毛,我记不清了,反正家里穷,再便宜也没钱买。”想看球怎么办?“爬墙头看,扒门缝看,那时候人小不起眼,跟着别的小朋友,有时候也能混进球场。”盯着场上队员用心看,跟着全场观众一起喊,这无疑是沙俊起最快乐的一段童年时光。
上小学了,就在学校操场上踢;放学后,在家附近的街道上踢。从第一天踢球开始,沙俊起就认定,这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好玩的运动。他在天津踢球的日子,绝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老师、教练指导,“就是看着别人踢得好,就跟着自己练,自己学。”
直到有一天,从体校来了一位足球教练,到学校选拔队员,他才第一次知道教练是什么样。也就在那天,他第一次对这个职业有了初步印象,并且铭刻在内心深处。当时遇见的那位教练身材高大、英姿飒爽,选拔队员的规刚也很简单,就是教练先示范一些基本动作,再让到场的孩子们照做,看哪些孩子模仿得好。
“他几十年前做的那些示范动作,我一直到现在都没忘。”沙俊起说,教练穿的那身运动服显得很精神,也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天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好好踢足球,我什么时候能踢得像他一样好,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教练?”
开远,足球注定的缘份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决定》。由此产生的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支边”人口迁移,一直持续到1966年。这一年,16岁的沙俊起追随时代洪流,主动报名支边,当时只知道去云南,具体地方和工作岗位未知。